作者:李旭光
编辑:王 珏
母亲琐忆
昨天才过春分,凌晨就下起雨来。这样早就下雨的天气属实是不多见的。小雨从早上一直绵延到下午,漫阴的天空笼罩在心头。有人说,雨是天泪。可泪为谁而落呢?
母亲去世已经有四个年头了。三年祭的时候,妹妹邀编一个集子,嘱我起名并题写书名。我取名为《阳光渐远》。意思是说,曾给予我们温暖和生命的母亲,已经如阳光般地慢慢西沉。她把更美好的生活留给了我们,尽管她的血和灵魂依然留在我们的身上,可我们在急剧变化的生活中却总也感觉不到幸福和快乐,多半是没有她老人家和我在一起的缘故。
我是初中毕业就按照所谓“四个面向”(指参军、升学、下乡、当工人)的安排参军的。记忆中的母亲,最鲜活的自然是小时候的哦一些事情。母亲是在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先是父亲从军赴朝参战,由于两个人是结婚在先,父亲就经常在家书中向母亲灌输革命道理,鼓励她也参加革命。那时正是建国的前夜,新生的红色政权需要大批的人才。已婚的母亲在与爷爷软磨硬缠的情况下,得到家人的支持,于年12月在前郭旗初中参加干部培训班,遂于翌年二月被派到二区任妇女干部。
记事的时候,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兄弟四人。虽然父母两个人都挣工资,但工资太低,日子很清苦。母亲生性要强,家务活洋洋都拿得起来、放得下。那时家里人穿的鞋多半要自己缝制。母亲有一个小“笸箩”,先是用柳条编的,“文革”时,我们捡来的大字报纸,还有顶针、锥子、鞋楦子一类女红用的缝纫工具。另外还有一个“铺衬包”,里面五颜六色的装了一些布头和碎布,做补丁和打袼褙用。外边是用块一米见方的小碎花布包起来。孩子们的衣服破了,母亲就把小笸箩和铺衬包、从箱子下面拿出来。箱子就装一些看起来是细软的东西,放在炕梢,用一块长木板搪起来,木板的下面用一块长条布遮掩住,里面装些杂物如前面所说的小笸箩、铺衬包、笤帚、苍蝇拍等。做鞋的时候,第一道工序是打袼褙。把面粉倒入清水,放到锅里加热后制成浆糊,用来把破布头,连同不能再穿的旧衣裤拆下来的布片,在一块木板上拼粘成大约有两三毫米厚的布片,称作袼褙。晒干之后,按照事先用纸剪出来的鞋样,用滑石笔在袼褙上画出鞋底和鞋帮的模型,用剪刀裁下来。鞋帮还好做些,衬上鞋里面就行了。鞋底则要纳出千层底来。纳鞋底时,要先到供销社买来麻坯,用麻锤纺出麻绳,再用锤子一针一线的纳。而且这种活常常是在晚间干,往往要忙到深夜。后来,家里买来缝纫机,我们兄弟的衣裤都是母亲亲手缝制。
母亲爱吃的东西很多,秋天是烀苞米、烧苞米,冬天是蒸豆包。蒸豆包时有一道工序是烀豆馅,把大云豆或是红小豆烀熟后用饭勺子在大铁锅里面捣成豆泥,加上糖后用手一个一个的攒成乒乓球大小的豆团。这些活儿母亲常拉着我和她一起干,所以记得比较清楚。比如缠毛线,一个人也可以把毛线挂在盘坐的双膝上,毕竟不如一个人只管缠,而由另一人双手撑着线,不住地摇动臂以随应缠线的人。而一有缠毛线的活儿,母亲总是叫上我。
母亲也爱养些家禽、家畜。但是为了贴补生活。记得刚从老工会俱乐部门口搬到一小学大门口时,三户人家合住一个大院,属于我们小家的空间突然大起来,母亲就开始养猪、养鸡,还养过鸭子和兔子,但兔子染上疫病,很快就死光了;鸭子食量太大,承受不了,只剩下养猪和养鸡。后来,家又搬到二中南墙外,还养过鹅和狗。这其中,养猪一项,对家里补贴最大。我从部队退伍回来,每年养的猪都要卖一口给食品公司,家里再留一口杀年猪。卖猪的钱,是家里办大事的唯一机动钱。
从母亲人事档案中的“自传”中得知,母亲年轻就得过淋巴结核,胃病,心脏病,肋膜炎等。我所知道的是,年的夏天,母亲得了肺结核。那时抗结核主要还是链霉素和雷米封。后来,医院从日本进口了利福平。我看到是用铝瓶装的胶囊,只粒,每瓶要48元,和母亲的月工资一样多,必须院长批准才能允许服用。所以,经常用的依然是口服雷米峰,加上静点链霉素。那时候,医院已不能正常开诊,母亲静点时在家里,要请护士为母亲兑药、注射。医院的护士,我就一次次地被派去请护士阿姨到家里。有时护士家里也有事,不留一件流露出来的怠慢与不快,使我在人生中过早地品尝到求人帮忙而又不能给予相应补偿的不易。
结核病是消耗病。发烧时候的母亲,满脸的潮红,浑身没有劲,就叫我帮她包饺子,吃“小锅”。吃小锅,就是为病人或家里主要劳动力单独做些看起来营养稍丰富些的菜饭。母亲吃的饺子是大白菜馅,从和面、熬馅、擀饺子皮、烧水等,都由我来做,母亲只是和馅和包饺子。每顿也只是包二十多个饺子,基本上没有肉,因为肉要凭票供应,又很少,每人每月只有几两。饺子煮出来,母亲总会让我也吃几个尝尝。八十年代我到白城工作,一次母亲去白城看她的孙子,适逢结核病复发。发烧之后,冬天里热得不行。我就到街里的商店去找,还好,见到一个卖西瓜的商贩。由于已进入冬季,当地的西瓜市面几近绝迹。所以,尽管找到仅存的西瓜,口感已远不如应季的好了。回到家里,母亲边吃边说好!凉快!后来我上初中,到砖厂劳动,牧群每天为我带中午饭,特意加工了一些糯米,为我带糯米豆包,吃了以后一下午都不觉得饿。母亲每次都把饭盒装得不能再满才罢手,其实也只是做给我一个人吃的小锅。
母亲给我吃小灶,还记得把她收藏多年,不肯示人的一件上衣改给我穿。那是一件女制服上装,有四个明兜(所谓悠兜),卡腰,开领。我初三的时候,母亲从柳条包里薄薄几层衣物中把这件衣服挑拣出来,下很大决心的样子把这件衣服给了我。衣服一穿出来在全班同学面前果然找来一片喝彩。因为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中学生的衣服清一色黄军装。结婚之前,母亲为我和妻子准备新婚时的服饰,特意乘公共汽车跑了一趟省城。我从部队退伍时带回来的一堆大枕巾,战友送给我的一个提花棉布床单等母亲都刻意留到我的婚事时拿出来。一个为母亲、为女人的细心时那样自然地流露出来。
八十年代后期,我到白城工作。一次,母亲得了青光眼,医院找以为老同志看病。也巧,正赶上省内一医院住诊,通过关系,破例安排母亲也就便做了手术。手术当天,妻子在学校当班主任,学校请不下来假,父亲又不在,单只医院。签单的时候,只好由我在亲属栏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眼睛的手术人们不是那么重视,母亲要自己走进手术室。更衣的时候,我抱着母亲换下来的还带着体温的上衣,既有一种为儿子的责任感,又有着对母亲手术的担心。术后,还安排施术的教授到地委壹号宾馆进餐。记得有一道菜是俄罗斯鲟鱼,鱼有脊骨是软的,绿色。母亲的眼疾很顽固,经常复发,也记不清在母亲的眼病和后来的介入术中,我为母亲的手术签了多少次名字。
母亲的性格非常刚烈,但对儿女则展示出极大的耐心和万般的慈爱,我参军到开原,也只有半年的时间,母亲就带着弟弟到部队去探望。到了部队,母亲被安排到招待所,执意地看了我住的宿舍,还约机关的协理员作了长谈。后来,协理员还对我说,你母亲是老革命呀!她真有水平呀!云云。可能这几句无伤大雅的对母亲奉承的话,正是母亲琐期待的,她是想以此来抬高儿子在部队首长心目中的地位。那次带弟弟,还逛了开原的公园、商店,带来的一些葵花籽、糖块、鸡蛋等食品,都分给了我的战友。警卫班的战友们为了表达心情,夜里到我们自己种的菜地里抠了一些土豆和花生,拿回到招待所,用铝壶煮着吃。弟弟把招待所的床单弄脏后,母亲不顾旅途劳顿,自己拿去洗,还要为我洗衣服。我告诉母亲,我已经学会洗衣服了。母亲问我,怎样洗衬衣,我说,主要是领口、两个袖口,要重点洗。母亲听了后笑了。当时,刚刚参军,又赶上五好战士半年初评,我被评上五好战士,母亲很高兴,我就催她造修动身,母亲自然是舍不得离开部队的。动身时,眼泪流个没完,使我想起从军那天。
本来,离开家乡那天,谈好母亲和父亲不到火车站送行,可送新兵的列车刚进站,我们开始登车的时候,母亲又跑到火车站。她在涌动着的人浪里,哭着、喊着,一遍遍地踮起脚来呼喊着自己的儿子,我由于事先和母亲有约定在先,也就没有挤到闷罐车的门口处张望,而把机会留给同样是新兵的那些老乡。偶然间听到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唤,看到母亲泪人一样地挥动着手臂,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下来。是啊,这是一个母亲,也只有一个母亲所能够给予她儿子的呼唤与泪水。而今,母亲已然长逝,这样的呼唤和泪水也与母亲一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请 (按住图片三秒钟,即可添加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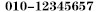 E-Mail:
E-Mail: